全国咨询热线:13501369536
全国咨询热线:13501369536
国有资产流失犯罪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一类犯罪的统称,泛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国有财产的管理者、占有者、使用者主观上有罪过,客观上造成了国有财产直接或间接的损失且数额较大的行为。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无“国有资产流失罪”这一罪名规定,但刑法条文(包括刑法修正案)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的共有25个罪名,大致可以分为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类国有资产流失犯罪,贪污贿赂类国有资产流失犯罪,渎职类国有资产流失犯罪三类。其中司法实践中常发的并经常容易引起争议的犯罪,主要是贪污罪、私分国有资产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等。下面对国有资产流失犯罪司法认定中遇到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研讨:
一、国企改制中隐瞒国有资产行为的定性
当前,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行为人隐匿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定性,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犯罪认定中颇有争议的一大问题。隐匿国有资产的行为特点是:行为人是原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是主要负责人,有的是管理层;作案手法是在资产评估机构拟评估改制企业资产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采取虚报债务、隐匿、转移资产等手段隐瞒国有资产,并骗取资产评估机构确认;企业改制后,行为人一般任新企业的负责人;原企业有的少数人成为股东,有的是多数人成为股东。上海市近年来就曾发生过几个这样的案例:
案例一:被告人袁某、邱某分别任上海城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城投)总经理、总经理助理。两被告于2001年至2002年在上海城投转制评估过程中,采用改动上海城投对外投资单位上海弘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弘安)会计报表的手法,故意隐匿上海弘安应返上海城投利润及收益计47万余元;采用隐匿上海城投下属东陆管理处挂在帐外业务收入的手法,隐匿资金计91万余元。两项合计138万余元。上海城投转制为上海民盈城投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民盈)后,于2003年1月至2004年3月间,袁某、邱某经董事会决定,以上海民盈名义,将上述隐匿的资产以分红利和送股的形式,按照比例分配给全体股东。
案例二:通产置业原系于1995年由上海中交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和上海市南市区市政建设总公司合资成立的国有公司。2000年2月至2001年11月间,通产置业参建上海盛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松江区新桥镇的“盛世香障苑”别墅项目,并向盛侨公司陆续支付612万余元人民币(按协议15%应付1100余万元人民币)。2001年10月,盛侨房产将8套别墅交于通产公司。2002年2月至2002年12月,通产置业将其中的3套别墅以出售等形式得款后冲抵应付盛侨房产投资款,多余389万余元以往来款入帐,尚有5套别墅暂留盛侨房产。2002年8月,通产置业即将改制成私营企业,进行资产评估时,被告人黄某、吴某(系公司的经理和副经理)授意公司会计林某将向盛侨房产的投资款以其他应收款项项目入帐予以冲平,从而故意向评估公司隐瞒该投资款的收益部分,不进行评估,至通产置业改制时为负资产。2002年12月,黄某向上海美洲星实业有限公司借款160万元,连同资金来源于通产置业的上海亿田工贸有限公司的20万元,共计180万元,作为黄某指定的6个人名义购买通产置业的500万股权。该6人是:赵某即黄某妹夫(54万元)、陈某(45万元)、徐某(27万元)、黄某(27万元)、韩某(18万元)、杨某(9万元)。自此,通产置业改制成私营企业。2003年2月,根据犯罪嫌疑人黄某的授意,吴某将盛侨房产支付给通产置业的160万元款项还给上海美洲星实业有限公司。在个人未实际出资的情况下用通产置业180万元购买股权控制了改制后的通产公司,犯罪嫌疑人黄某、吴某获取人民币973万余元。
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新出现的行为手段的定性五花八门,其中不少被认为“法无明文规定”而作非罪处理。有的认为应定贪污罪,但认定贪污数额应以被告人在改制后的企业所占股份比例来确定,其余部分作为造成的国有财产损失在量刑时予以考虑。⑴有的认为应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隐瞒国有资产案件的行为人在国有企业改制中,为了新企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滥用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职权,采取虚报债务、隐匿资产的手法,隐瞒国有资产,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符合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的特征。⑵有人主张应定私分国有资产罪。主要理由是:行为人隐瞒国有资产目的是为了企业改制中各股东减少购买国有资产的货币支出,而减少货币支出等于私分了国有资产。
我们认为,首先,隐瞒国有资产案件构成犯罪。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企业改制之机,为了改制后新企业股东特别是个人的利益,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虚报债务、隐匿资产等手法隐瞒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其行为侵犯了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关系,破坏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在这几年国有企业改制中,这种行为已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不对其以犯罪追究,而仅以退出非法所得了事,就难以遏制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这股歪风,难以保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因此,必须也应当以犯罪追究。
其次,企业改制中隐瞒国有资产的行为也不构成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1)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不是目的犯,即不属于以实现某种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件的犯罪。因此,行为人并不具有通过自己行为给公司,企业和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直接追求,隐瞒国有资产案的行为人却以非法占有国有资产为目的。(2)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行为是滥用职权,它与国有资产重大损失间的关系是“造成”和“致使”的关系,而不是把行为直接指向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进行直接的侵犯。在因徇私而滥用职权的情况下,私利之所得与国有资产之所失并不等量,前者往往小于后者,而隐瞒国有资产案的行为人却把行为直接指向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的所有关系实施直接的侵犯,并对其进行等量平行转移,即把国有资产等量地、平行地非法转到行为人个人或转制后的私营企业。
再次,隐瞒下来的国有资产表面上是被新企业非法占有,实际上是被行为人等股东非法占有。在部分国有资产被隐瞒的情况下,行为人等新企业股东在购买国有资产时就可以少付被隐瞒的那部分国有资产的价款。即使隐瞒的资产归新企业,其所有权也属于股东。因为改制后的新企业为公司制企业,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属于股东,尽管隐瞒下来的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仍在企业,但其所有权属于各股东。
最后,从案件实际看,隐瞒国有资产有的由个别人决定,有的则由单位领导机构集体决定,所隐瞒的资产有的被个别人或极少数人非法占有,有的则私分给较多的人。因此,隐瞒国有资产案件有的是贪污,有的则属于私分国有资产。什么情况下是贪污,什么情况下是私分国有资产,这关涉共同贪污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界限。共同贪污罪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决策者是为自己或极少数人非法谋取利益还是为大家非法谋取利益。⑶因为“集体私分”是私分国有资产罪的重要特征,它既指决定私分主体的集体性,即私分经决策机构集体研究决定(从实际情况看,私分的决策者为了分散风险,避免个人承担责任,也往往会与决策机构中其他成员通气、研究),更指私分对象的集体性,即将国有资产私分给单位全体成员或多数人。因此,在私分国有资产罪中,私分对象除了私分决策者外,还有单位内部较多的人;同时,在私分对象是“多数人”的情况下,其“多数”的划定,必然根据某一客观事实,如某年之前进单位工作等。而共同贪污犯罪则不然,它是决策者为自己或极少数人非法谋取利益,其决策者及参与策划者的范围往往与分得赃款者的范围一致,且其范围的确定并非依据一定的客观事实,而是根据共同贪污犯罪的需要。第二,分得赃款者是否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行为。在私分国有资产罪中,决策者之外占多数的分得赃款者未必具有私分国有资产的故意和行为,有些甚至连钱的性质和来龙去脉也不清楚,只是被动地领到单位的“奖金”、“福利”而已。而共同贪污则不然,各分得赃款者主观上都有共同贪污的故意,即明知自己在与其他人一起进行共同贪污犯罪,客观上都有共同贪污行为,即都参与实施了作为共同贪污有机组成部分的行为。第三,分配赃款行为在单位内部是隐秘还是相对公开。私分国有资产罪是“以单位名义”进行的,因而在单位内部较为公开,不仅私分对象知道单位发过钱,而且私分对象范围外的人也往往知道单位发过钱,只是由于自己不符合某种条件,因而未能发到。而共同贪污则必然偷偷进行,讳莫如深,除参与策划并分得赃款者外,绝不让外人知情。总之,根据上述三个方面,不难划清二者的界限。
根据—上述关于共同贪污与私分国有资产的区别以及前述的隐瞒下来的国有资产一般转入新企业归股东所有的实际,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凡原企业中只有隐瞒国有资产的参与策划者、知情者等极少数人成为新企业股东的,应认定为共同贪污;凡原企业中所有人或者根据某一标准划定的多数人是新企业股东的,应认定为私分国有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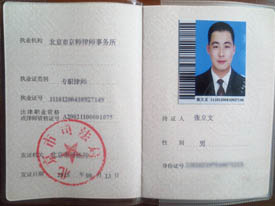
律师执业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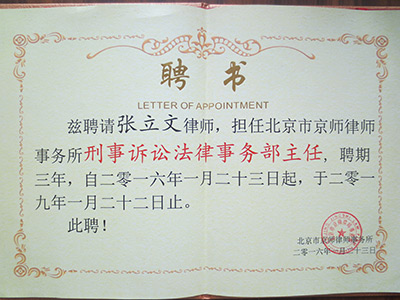
京师律师事务所刑事诉讼部主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

中国法学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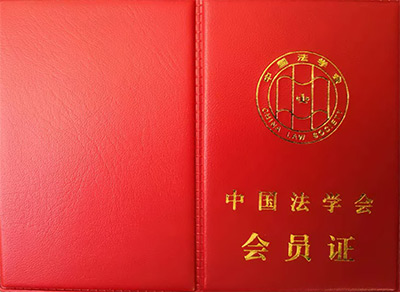
中国法学会会员